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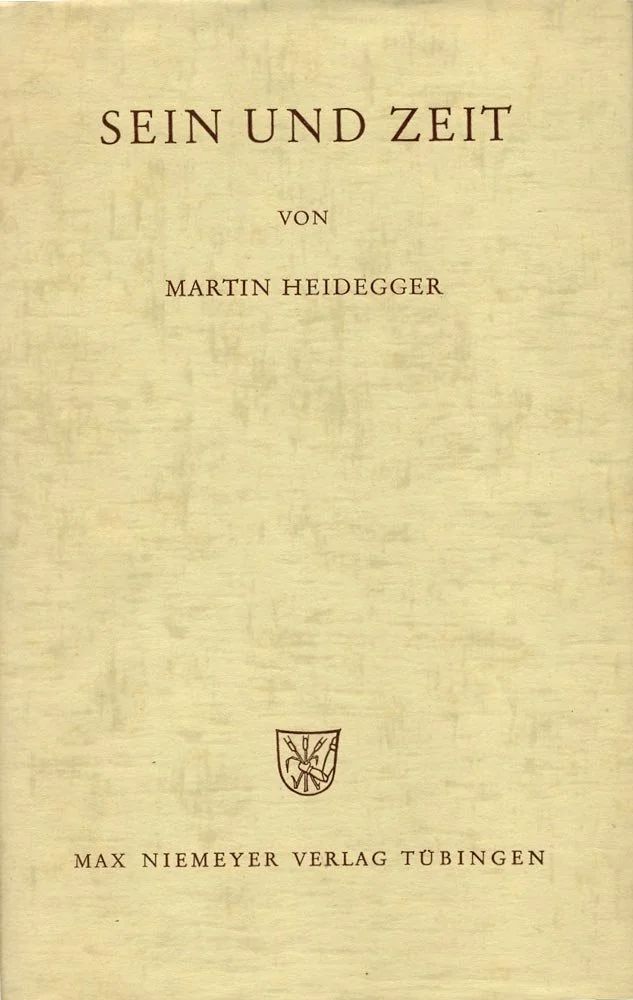

(图源网络)
启蒙哲学家经常提出这样的指责,“所有这些人,如海德格尔、Gadamer和梅洛·庞蒂,都只强调了人的有限性和迫切性,他们完全忽视了普遍性。”这是一种误读。他们只是指出,每一束光都预先假定了一抹阴影,每一处光明都预先假定了一片黑暗,所有理性都预先假定了非理性。所以,内在性和超越性,或者说有限性和无限性之间的也是这种关系,是以一个对话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在会议上讨论的内容,这就是我们如何引入对话关系的概念的。我认为这是超越启蒙理性主义的关键一步。
杜:我认为,我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思考人类。这种抽象的普遍主义集中在原始状态、普遍的(非具体)自我和一个人完全脱离身体的想法,不涉及历史、社会,没有被历史化或语境化。我认为人们越来越担心这种特定的哲学风格。相反,我们应该把具体的人性(humanity),或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作为出发点。如果我们采取这种特定的方法,就有变得非常狭隘、非常局限的危险。但我并不那么担心。我认为问题在于地方知识的全球意义。现实中,在学术界和整个知识界,大多数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都来自西方:巴黎、伦敦和纽约。现代化理论、构建和解构,他们都来自欧洲。
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大概是20世纪60年代,我与罗伯特 · 贝拉(Robert Bellah)进行了一次对话,我们一致认为,下一代真正的全球思想家,或者当时我们所说的“世界思想家”,至少应该承认,他们愿意与非西方世界接触交流。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所谓的世界哲学家故意将自己局限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然而,实际上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比如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也许还有梅洛·庞蒂,他们只关注现代西方,对外面的世界有些漫不经心。换句话说,(他们与外部思想的关系)就像西方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你能够面对西方的挑战,那么其他事就能步入正轨。我想这让我想起了阿什 · 南迪。他来自印度,非常有创造力。他说,他在剑桥从来不觉得舒服,因为坐在他旁边的亲密朋友似乎认为“你的现在是我们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是你遥远的未来。你现在才开始这种单线性的发展……”

【北京论坛(2011)】轴心文明的精神滋养——杜维明对话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
杜:这是一种侮辱,但是很多人都这么认为。这就像德里达在中国说不存在中国哲学一样。在中国,一个主要的争论是我们是否有中国哲学,或者简而言之我们在中国只是做哲学。这对我来说很奇怪。我们从特定的欧洲中心主义转为更广阔的世界视野。我认为你展示了在印度和中国的这种接触。罗伯特 · 贝拉也完成了关于德川宗教的博士论文。当然,他转入研究了那些美式场景,心灵的幸福和美好的社会。但是现在他的宗教理论是全球性的。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后,他又回到了宗教理论。我认为如果他的书出版,那将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查尔斯 · 泰勒可以被包括在内,但他的整体取向与《世俗时代》一书有关。然而,我不会直接和他谈及,因为这本书还是非常关注现代西方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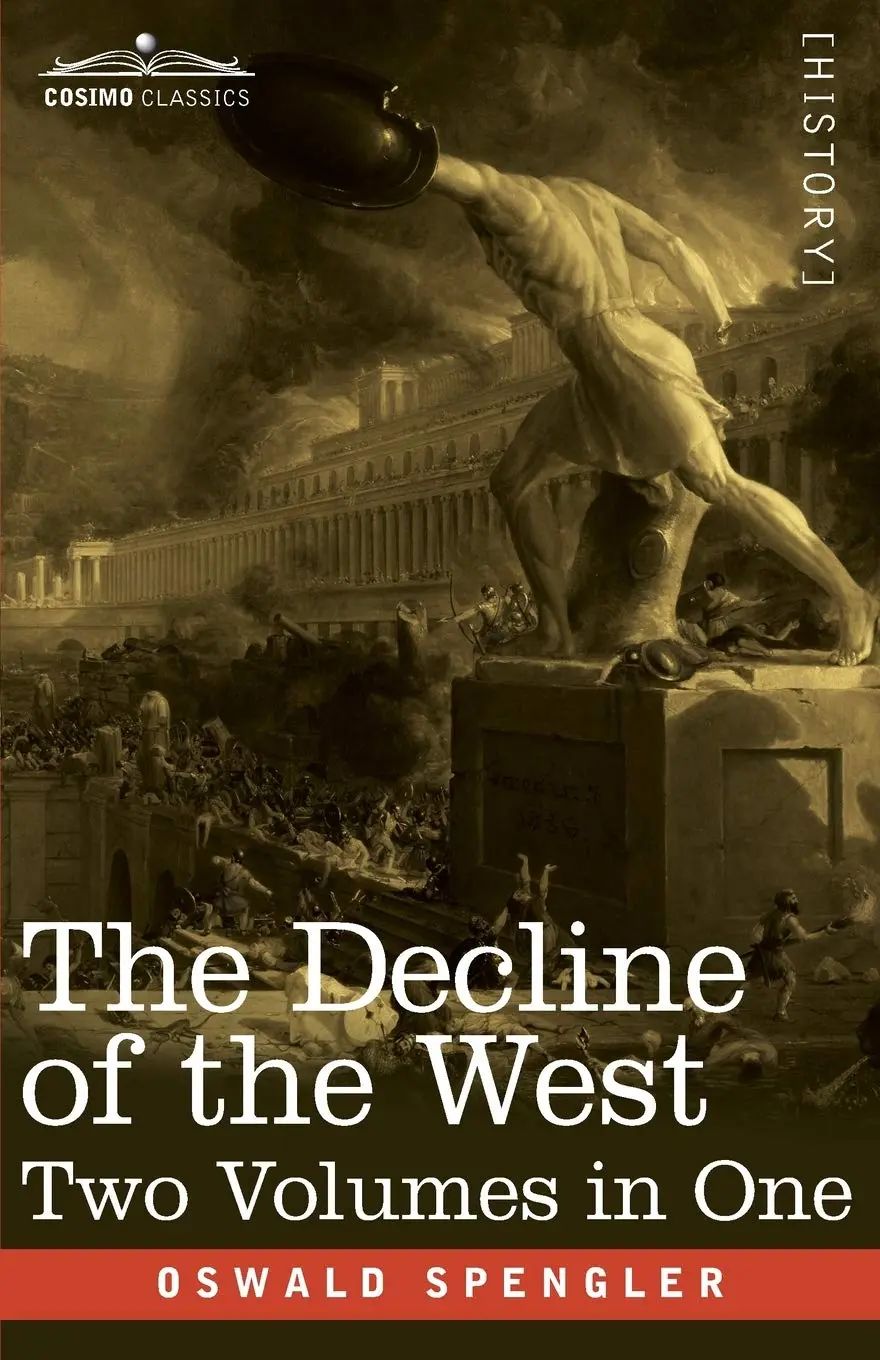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 Two Volumes in One. Cosimo Classics, 2020.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之后—— 一方面是马歇尔计划,另一方面是同盟国军事占领日本、或者把日本变成小弟—— 美国从一个伟大的学习型文明:一个从法国学到启蒙运动传统、从德国学到科学技术、从英国学到文学和语言的文明,变成一个有时非常傲慢的传道型文明。
多:碰巧我写的上一本书——这本书现在尚未出版,但将在今年秋天出版——是关于自然的。书名叫《回归自然?》在那本书里,我提出了一种我称之为“生态学式颠倒历史”的东西,一种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叙事相反的历史。这是一部关于那些认真投身于自然的人的颠倒历史。换句话说,他们试图发展一种关于整体性、统一性和宇宙性的思想,而不是现代西方二元论的主导形式,比如关于身心、自我和外在自然的笛卡尔二元论。我从斯宾诺莎开始谈到莱布尼茨,从莱布尼茨到谢林,从谢林到伟大的浪漫主义者,然后是约翰·杜威,最后是海德格尔。最后一章提到了亚洲哲学,以及所有这些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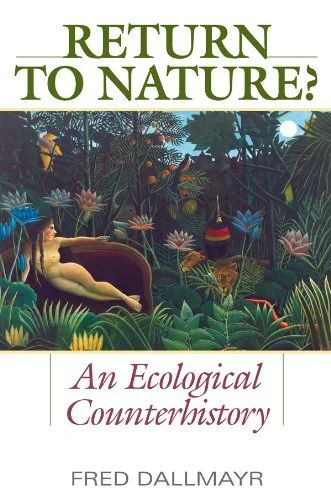
有了这个新的方向,我试图超越现代西方思想的二元框架,即笛卡尔框架。许多当代思想家仍坚守着这个框架,包括以不同方式坚持的哈贝马斯、理查德·罗蒂,以及米歇尔·福柯。遗憾的是,尽管在许多方面我与我们的朋友查尔斯·泰勒志同道合,但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至少在他最近的作品中,他正滑回到这种两分法之中。这种二分法分裂整体并让它不可能恢复统一。这一点尤为明显,在他的……

杜:作为一个作家,艾倍她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满月问题的图像。现在只有半个满月,所以是半月。但是月亮还有另外一面,不管你用我们的专业术语称之为“缺席政治”还是使用“缺乏”的概念。认为我们没有民主,我们没有科学,我们没有批判性的理性主义思考,等等。现在是时候让月球的另一面展现自己了。所以你提到的人类良知的完整性,必须是两者的融合,两者健康的融合。我认为地球(对人类)的挑战可能为这种特殊的思考提供了最后的机会。尽管考虑到制度、思考习惯、政治等等的限制,我对我们是否会致力于此感到相当悲观,但我认为每个人都应意识到,如果没有这种新的融合,没有这种新的整体感,没有真正的对话——我对“真正的对话”的定义是“对话文明之兴起”——(出现特殊思考的)可能性会非常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1世纪,一种精神人文主义将不得不蓬勃而出,成为各种不同信仰团体进行哲学和宗教反思的出发点。
换句话说,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儒教徒等等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我们是人。这种从进化角度对人类的反思表明,人类的出现是个非常重要的一般性事件。有些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不再是进化的结果;我们现在已经在塑造进化的方向。儒家的“伙伴关系”或“共同创造者”的概念可能会被扭曲或者完全被颠覆,(人)不仅变成人类社会的主要破坏者,也变成自然的主要破坏者。

我们现在肯定有这样做的可能,这就是浮士德精神或普罗米修斯精神——以牺牲我们自己的幸福为代价,无限地追求知识,以及财富、权力和影响力。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想到尤尔特·柯慎士的观点:也许21世纪的先知就是地球。地球将告诉我们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能帮助我们走出乱局的老师们,可能是有着倾听地球声音的想法的那些原住民中的长者。无论是夏威夷还是这里的原住民传统,似乎都拥有丰富的资源,而现代人却在不经意间失去了,所以……
杜:在11世纪或12世纪,有一位非常伟大的新儒家思想家名叫张载。他的《西铭》以一句美丽的话语开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认为自然是我们的一部分的观念不是一种想象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存在的现实。我们能感觉到。
这与海德格尔的观点大不相同,因为海德格尔,或许还有存在主义者,认为我们被抛向世界,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存在就是为了自我证明不断做出选择。这种有限性,也是祁克果(索伦·克尔凯郭尔)的生病直至死亡的观念,有一种巨大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尤其存在于科学技术中,它们隔绝了我们和存在的声音。现在出现的新人文主义,即精神人文主义,必须要有一种非常全面的、包容一切的整体感,而这种整体感建立在一种能帮助我们超越内在疏离感的自我修养的基础上。所以,正如你所指出,有限性是无限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有限性就是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类工程的局限性和走向死亡的必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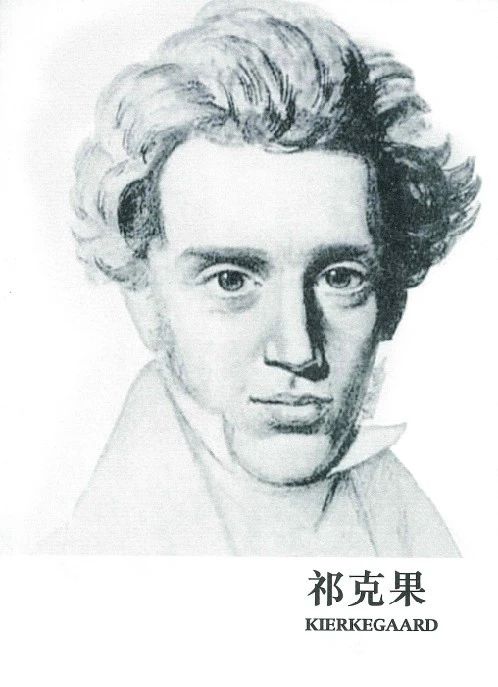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在香港参与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时,我发现代表儒教的合作伙伴,如秦嘉懿、狄百瑞、白诗朗和南乐山都是基督徒。这不仅是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也是基督教间的对话。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分辨出儒家式基督徒和非儒家式基督徒的区别。我现在的答案是,如果你是具有儒家思想的人,你必然关心政治、会参与社会事务并且具有文化敏感性或者了解文化知识;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拒绝政治、否认凯撒式世界的合法性并且认为文化相对信仰而言是多余的也是完全正常的。对佛教徒或其他宗教信徒来说也是如此。然而,作为一个儒家式基督徒,你就是不能不参与。这就是为什么有左翼佛教(人间佛教)和整体佛教势力。尽管儒家学说不是一种宗教,但儒家传统的宗教性或精神性也能够作为人类事业的一部分共享。所以,虽然这个观察结果有太多的假设,但是我确信此处存在一些意涵丰富东西。

我认为,在21世纪的新人文主义中,我们至少要将这四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认真考虑。在理解一个人时,除了身体意义上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有对心(mind and heart)、灵和神的理解。此外,还有社区,它必须是高度差异化的,但也是完全综合性的。我们可以把它从个人扩展到家庭、社区和自然界、世界,甚至更远。地球或自然维度表达了重建和谐的、可持续的关系之需要。在这个概念中,虽然天不再是那个不可言喻的、有着绝对的力量他者,但是,我们却永远不能通过理性的推理来理解之。因为我们是伙伴,天或神内在于在于人的。人不仅仅只有内在性,因为没有超越性做参照,人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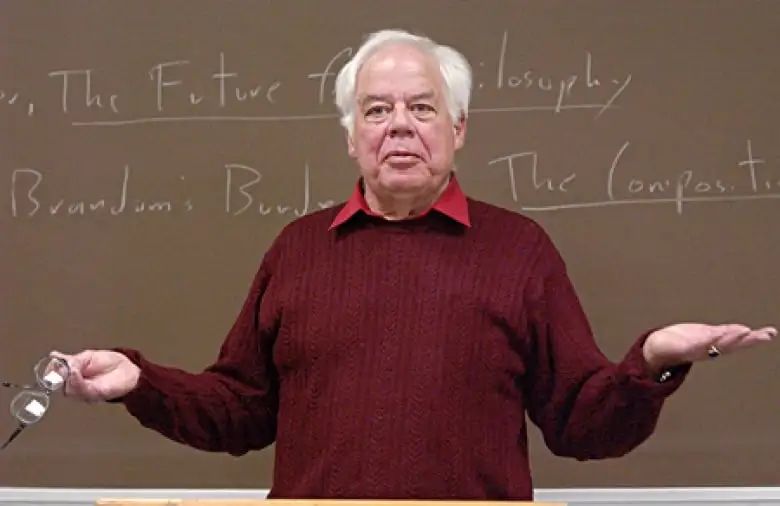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祁克果有三个非常独特的领域:美学、伦理学和宗教学。在这种新视野中,伦理或道德必须植根于人类的基本情感。因此,美学与伦理学完全没有冲突,伦理学也不是简单的受规则支配的行为。伦理学不仅要延伸到社会之外,还要延伸到人类世界之外,这样才能与天相通。所以美学、伦理学和宗教是一个连续体,并不是完全分离的。我承认,分析作为一种自我训练方式以及一种启发式设备,绝对是重要的,但人类应该完全舒展开来,与现实融为一体。
英文:黄琦
翻译:王胤莹
校对:王建宝,陈茂泽

Copyright@2014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京ICP备案1253235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五号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4号楼 技术支持:i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