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全球对话与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第十届“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2021)近日在京举行。根据会议既定日程,来自海内外的15明专家学者于2021年10月16日下午在线上出席了论坛小组研讨之“十年未济:对话的践行与机制构建”。

当然,正如与会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赵东明认可的“(比较)宗教学之父”——英籍德国学者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所提出的观点:“只知其一,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 亦即:“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宗教也不懂。”。赵教授据此认为,只有对其它宗教进行客观深入地理解,知道其它宗教在说什么,才能真正的进行对话与交流!
本组十五位学者的发言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文明对话的机制构建:以仁为本,出入两希

韩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仁道——多元文明对话的价值基础”。他认为“孔子贵仁”。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的一些基本价值——“仁、义、礼、智、信”,与西方一些观念一样具有普世价值,可以互相参照学习。
2001年5月,联合国“文明对话核心小组”(Group of Eminent Persons, UN)在都柏林讨论文明如何对话,小组成员之一的孔汉思(Hans Küng)提出,要发展文明对话应该把儒家的两个基本价值和理念作为起点,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对话的目的不是说服,而是了解;了解的前提是自我反思;二是人道原则,即《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种共同繁荣和发展的健康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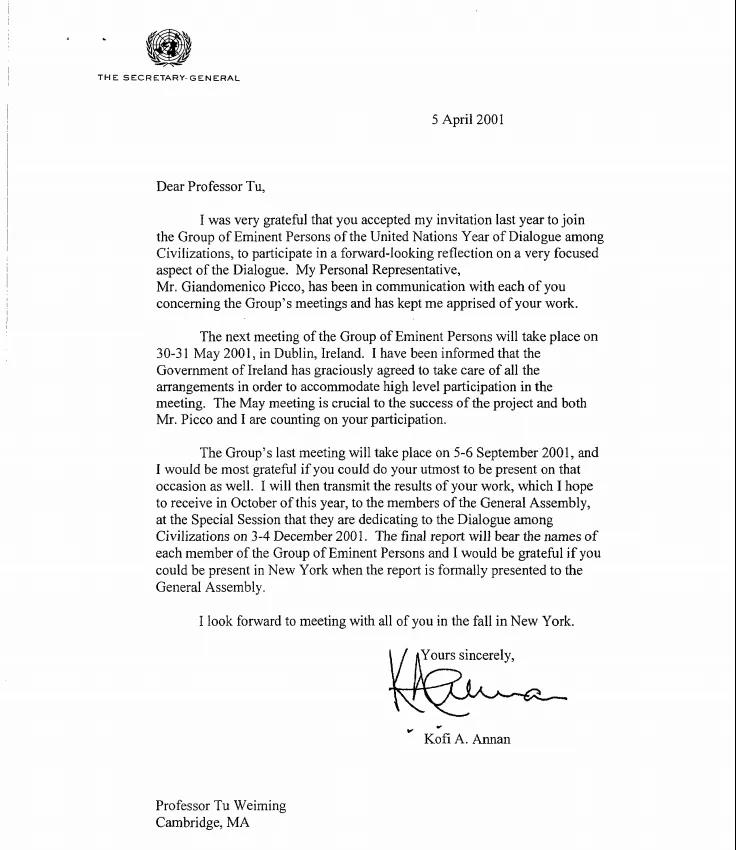
杜维明先生认同这个看法,他指出:有两个原则必须建立起来,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恕道”,“恕道原则的背后有一个仁道原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别人的痛苦我关怀,我的发展也有利于别人的发展。这两个原则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也是孔汉思认为的文明对话的两个基本原则。” (杜维明:《对话与创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32、92页。)
不同民族文明之间的对话,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世界上最早的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便继承了苏美尔、卡尔德的文学遗产,而其中关于洪水的细节,后又被犹太人改编收入《圣经》,并成为《旧约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吴元迈:《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化进程和世界文化》,《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中国古代文化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对话交流,形成东亚“儒家文明圈”。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指出:“不同文明之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 (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
避免文明冲突的基本途径是文明对话。“文明对话”可以通过阐发儒家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代替“文明冲突”。“仁”是儒家核心思想体系之核心,具有本元性、本始性、普遍性,是“人之为人”的底线、基本道理和最高境界。实现仁道的基本途径是“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是求仁之道,是儒家一贯之道。“仁道”的基本含义是“仁爱”,其可以成为不同文明对话的价值基础。“天下归仁”既是“仁”这一核心价值同心圆推衍的结果,也是儒家仁道逻辑演进的旨归,更是儒家仁爱之道的社会理想。立足于仁道的儒家圆融无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许教授题为“文明对话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造 ”的发言中也提到了2001年5月都柏林的这场对话。面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杜维明先生强调:“最重要的是中美之间需要进行核心价值的对话。人权与责任、自由与正义、理性与慈悲、个人尊严与社会和谐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他所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涉及自我、社群、地球和天道,注重身体与心灵、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世俗与神性之间的调和,从而为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提供指导和解决之道。
杜维明先生的文明对话理论既是对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回应,也为新文明观的形成提供了借鉴。“文明蒙尘”的中国开始为人类构建命运共同体,开始为地球创造文明新形态。

“冷战后末世书写中的西方/文明”是李教授的发言题目,她认为“文明有起落,历史无终点。” 西方文明的命运究竟如何,将由下一代的史家继续书写。
公元前一万年前,地球上原有数千个人类文明;但到了公元前2000年前,只剩下数百个。(赫拉利,《人类大历史》,页190。) 西方史家对于西方文明在近五百年来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抱着复杂的情绪,骄傲、自责兼而有之。今日西方大学更是几乎都认为帝国主义是现代世界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弗格森,《文明》,页192-195。) 在西方扩张的过程中,霸道的成份实多于王道;19-20世纪西方独霸全球,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沾染了太多亚非拉澳等地人民的血泪。

尤拉尔·赫拉利
1960年代,人类出现史上变化最剧烈、最速度、也最为普遍的一场社会大变革,突然结束中古时代生活,传统小农死亡,永远切断了我们与过去的血脉连结。不论是在工业国或落后国,农业人口都有所下降,而城市则挤满人潮。(霍布斯邦,《极端的年代》(下),页434-442。)
尽管西方近五百年已在世界各地大获全胜,但这些学者却觉得大祸临头。弗格森(Adam Ferguson)寻思:是谁杀死了欧洲基督新教?或许如韦伯(Max Weber)所说,资本主义精神必然将摧毁自己的新教伦理源头。
“‘西方’很复杂。它不是铁板一块。”亨廷顿忧心文明冲突;弗格森唯恐基督新教伦理不再,他对西方唯一抱憾的是今日欧洲基督新教信仰日渐式微,以致西方人工作伦理不彰;他甚至将当代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归功于基督教在中国的日益风行, (弗格森,《文明》,页356-360。) 令人感到错愕。巴森(Jacques Barzun))感叹西方文化分崩离析,就政治而言,20世纪后期最强烈的趋势为分离主义。近代西方最大的政治产物——民族国家——已经受到打击,英、法、意大利、西班牙国内都有不同族群想要独立建国。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断言资本主义正自取灭亡,戴蒙(Jared Diamond)悲悯全球环境崩坏,而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则冷冷预告人类将被生物算法掌控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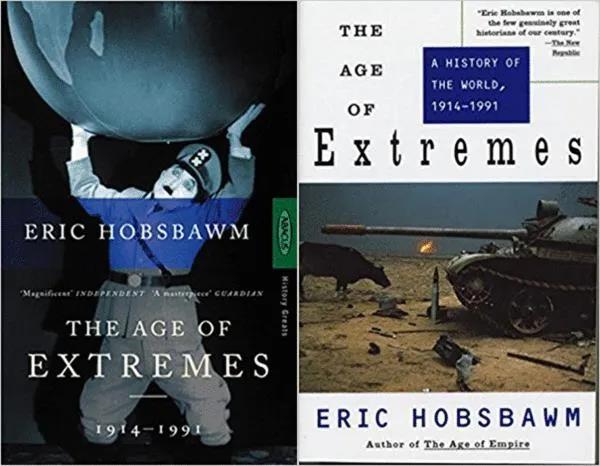
《极端的年代》的不同版本
霍布斯邦的结论是:19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风行,最后站在共产主义的废墟上宣布得胜。但是胜利的一刻,也是其运转不灵的开始。市场经济胜利了,但是它已难掩其社会与文化的空虚。(霍布斯邦,《极端的年代》(下),页514。) 就像马克思(Karl Marx)所预言,资本主义是一股具有不断革命性的大力量,会将一切解体,甚至连它生存所寄的“前资本社会”也不放过,而它自己也自然难逃一死。(霍布斯邦,《极端的年代》(上),页27。)

赵教授的发言围绕“全球宗教对话与共用未来——一种‘宗教对话’及‘思想借用’的尝试与共用”展开。“笛卡儿式的焦虑”从欧洲蔓延到全球。历经几劫几难的佛教会有怎样的参考和反思呢?
赵教授从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卡尔‧拉纳(Karl Rahner)、卡尔‧巴特(Karl Barth)、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等几位现代”基督宗教“神学家的某些观点出发,尝试进行一种宗教哲学上”思想借用”的论述与说明,以作为现代社会中“基督宗教”与“佛教”之对话的可能契机与进路。
此外,他还尝试借用现代西方“基督宗教”(Christianity)神学面对“现代性”(Modernity)的议题(佛教与「现代性」此议题的论述,可参考:林镇国,《空性与现代性》,台北:立绪文化,1999。)所能提供给佛教思想的一些参考、反思与对话。以做为“全球宗教对话与共用未来”的一个讨论面向。发言中,赵教授还分享了两个理论模型。

“宗教对话”的三种著名理论模型图示
天主教普世神学家保罗‧尼特(Paul Knitter),在《宗教对话模式》(Introducing Theologies of Religions)一书中又区分四种宗教对话的模式,亦即:
置换模式(Replacement Model):认为基督教最终将取代其它所有宗教;这接近“排他论”或“个殊论”。
成全模式(Fulfillment Model):其它宗教中其实已有基督教的部份真理,但最终的救赎实现,仍需要归在基督名下;这接近“包容论”(兼并论)。
互益模式(Mutuality Model):各种宗教都是救赎的有效之道,并不是谁取代谁,而是互相学习;这接近“多元论”。
接受模式(Acceptance Model):各种宗教有着不同的语言论述,彼此之间是无法比教或取代的,因而只能彼此做个好邻居,而不应互相干涉;这亦接近“多元论”。
(二)文化认同之建立:儒学思想抉微

张昭炜教授长期关注方以智,用力颇深。曾经到安徽省博物院抄写方以智的《易於》一书,惠泽士林。他的发言题目是“明清之际‘中国’之‘中’的哲学文化抉微”,对“中”做了精彩阐述。在建立文化中国的认同的艰难历程中,明清之际的方以智越来越重要了,不说超过了黄宗羲、顾炎武月王船山,至少是比肩之巨擘。他认为,以“中”为基础的礼乐文化属于中国特有,周公之后,孔子继之。
“中国”之“中”常被解释为“中间”,亦可解读为㐅(中五)。较之于“中间”,㐅在解释无形与有形相交、中与四方关系、中与礼乐的对接、中的时间调适能力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㐅在旋转中形成向心力,亦可以说㐅诠释的“中国”具有天然的文化凝聚力。“中国”之中的三个层次隐含着神圣与使命,地理与文化之中体现在作为旋转中心的㐅,而天地之中体现在天地相交之㐅。
在明清鼎革之际,中国文化饱受摧残,大思想家方以智为中国文化托孤,他思考的“中国”包括天地之中、地理之中、文化之中三个层次,㐅是三个层次的共同基础。㐅在语义哲学中包括正中、圆中与时中;在地理政治视野中,形成“环四中五”的混合双旋模式;在文化层次,可诠释为中宫、太极、皇极,以及以礼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㐅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与文明的融合力,这对于我们继承古老“中国”的文化遗产,展现中国的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教授还指出,由国名造成西方思想家对于“中国”之中哲学文化的不理解,不仅表现在明清之际,直至今日,我们尚未摆脱以“瓷器”翻译“中国”国名的困境,这也提醒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与从事中外交流的翻译家,应多从哲学、政治、文化等多层次展现“中国”的丰富含义,发扬作为“天地之中”的神圣与使命,增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张辉博士的发言围绕“道德教化与实质正义的追寻”展开。张博士认为,孔子反对铸刑鼎与他提倡道德教化治国与追求实质正义的思想密切相关。在治国的方式上,孔子提倡“为政以德”,强调为政者以身作则,教化百姓,反对实行刑罚治国,认为刑罚无法消除为恶之心,不能从根本上防止犯罪,并非首要的治国方式,只是最后不得已的选择。在对待法律上,孔子警惕法律自身具有局限性,认为社会治理单纯依赖固定的法律形式难以保证公正,容易造成对实质正义的背离,因而相比于单纯依赖法律程序,孔子更看重行为本身的正当性,追求内在的实质正义,而不是机械遵从外在的法律形式。
孔子提倡道德表率、德行教化,反对专恃刑杀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奠定了后世中国政治实践中德主刑辅的传统。当然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孔子也没有完全否定刑罚的作用。杜维明指出:“仁作为一个内在的品质并不是由礼的机制从外造就成的,相反,仁是更高层次的概念,它规定着礼的含义。” 孔子强调仁的优先性和根本性,背后无疑透露出对实质正义的关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孔子对仁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是否认礼的作用,孔子追求仁礼互动基础上的统一,但前者被认为是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Copyright@2014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京ICP备案1253235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五号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4号楼 技术支持:iWing